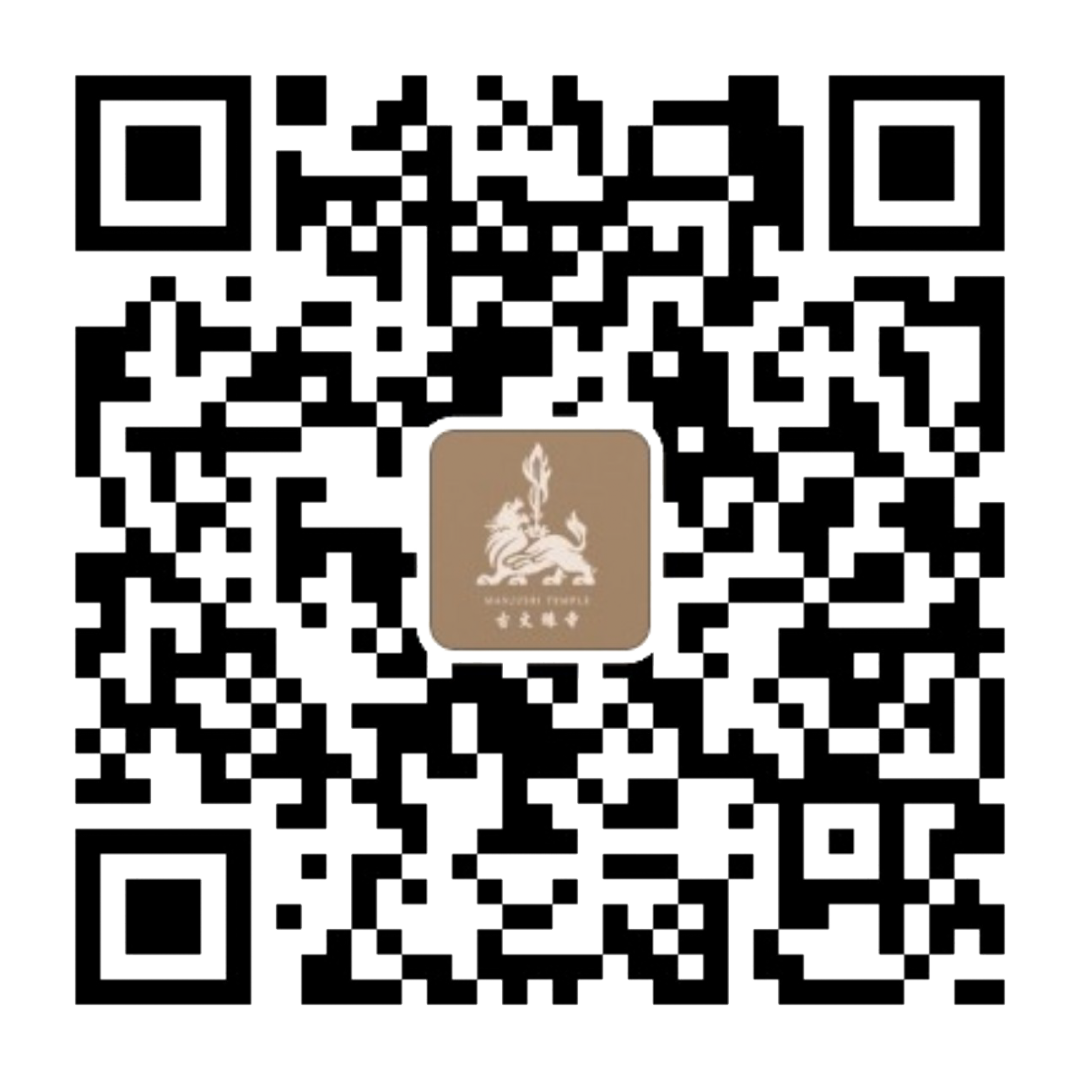智能时代的生命思考


推荐音频同步收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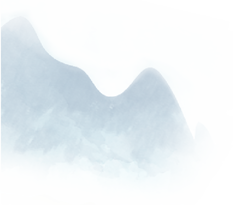
大家在寺院,就好像家家户户的代表一样,你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代表着自己血脉的传承,代表着历代的宗亲。
生命是有这个传承的。“天地生万物”,在宇宙这个时间轴上,生命有相续性,我们的列祖列宗、九玄七祖的每一个生命,都曾经沐浴在日月的光明中。
所以,古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人类已经形成了文明形式,已经有了族群,有了国家的形式,那国家的最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左传》里刘康公的话,一个是祭祀的“祀”,一个是“戎”,保卫的意思。
“祭祀”能把我们的生命从低维空间超度到高维空间,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而转凡成圣,这是“祀”的主要核心,这是每个国民,乃至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参照物,甚至是具体的内容。
“戎”是一种保护,能保护大家安定在道上,保护向道的次序不紊乱。
这就是一个国家两个最核心文明的内涵,也可以说,祭祀承载了道,戎表现为德,是维护这个次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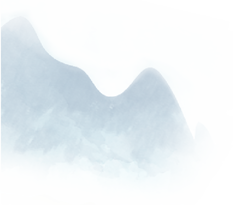
这恰恰是文艺复兴以来一个很重大的人类课题。尤其是当物理学在机械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我们就开始轻视道学的重要性,把拜金、拜物抬到了社会的主流高度。
实际上,所谓的哲科体系,只是在整个人类的学问中当的一个体系。哲学的逻辑本身就是为了理解、修证宗教的理论和目的,乃至科学的验证,也是帮助我们提升的。本来宗教是哲学之母,哲学是科学之母,现在却把哲学中关于道的部分淡化掉了,甚至忽略不提,只谈哲科体系这一方面的理论。
现在,机器智能已经很强大了,又逼着我们要做回人了,因为要想驾驭强大的机器,人类必须追寻智慧,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清明来到这里思考:为什么民德要归厚?因为只有民德归厚了,才会有道的土壤。老子曾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德必须要厚重,道的“树苗”才能冒出来。德很稀薄了,慢慢地,当这种文明的自觉成分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开始有暴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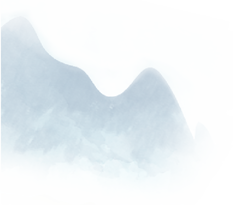
甚至如果个人行为对别的生命、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的时候,寿命虽然还没到,却宣布了死刑。也就是说,除了自然的生物体,我们的行为也可以决定自己是活着还是死去。
这个时代也在逼着人类去思考,我们不能再沉溺、陶醉在这个游戏或者科技的玩具里了,而是要再一次去反省,再一次回归到人的本位。
如果文艺复兴是对数理化的一次振兴的话,那现在需要更重要的一次复兴,就是道学的复兴。文艺复兴也是把古希腊的一些哲科思想理论加以放大,而现在更需要像屈原的《天问》中那样深层的思考。他在这首长诗里提出了一百多个关于人生与宇宙的疑问,天地万象、贤凶善恶、存亡兴废……这些现象与事物使他困惑,又引他思索,虽然他最终并没有求得一个答案,但他的这些疑问代表了人类社会普遍的困惑。
所以,我们佛教徒,尤其是住在寺院里的人,是从社会的资生产业里解放出来的人,不需要为了衣食去奔波,那我们做什么呢?是需要我们在道德上有所建树的。我们是专业为了这个道德而修行的人,我们要能为道德做证明:道是什么?德是什么?道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这些是我们佛弟子要去用一辈子要去思考和践行的本分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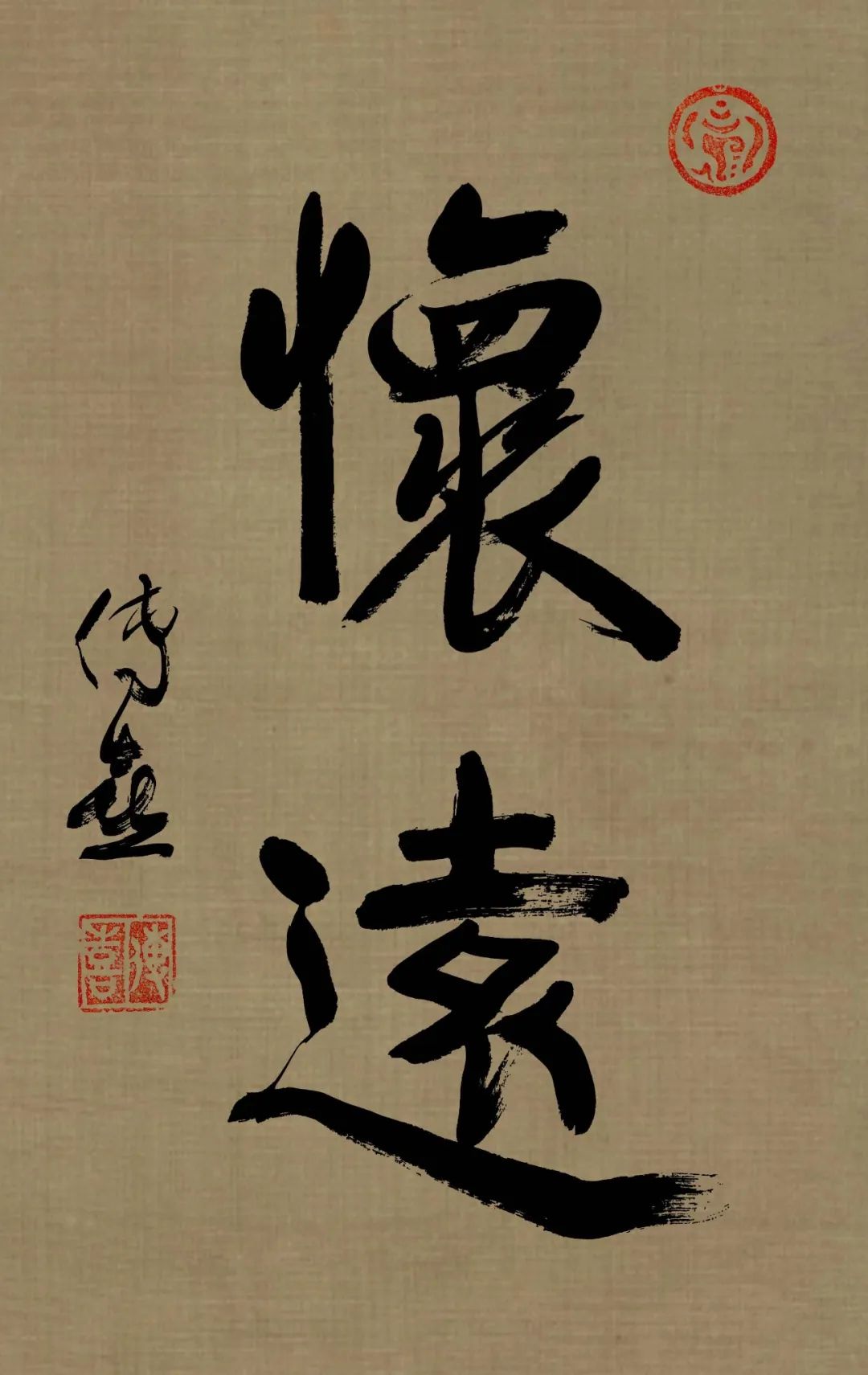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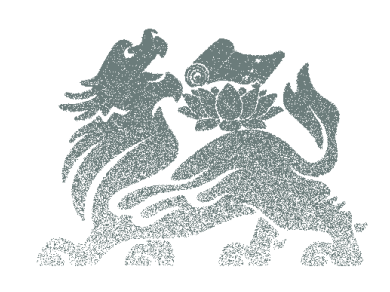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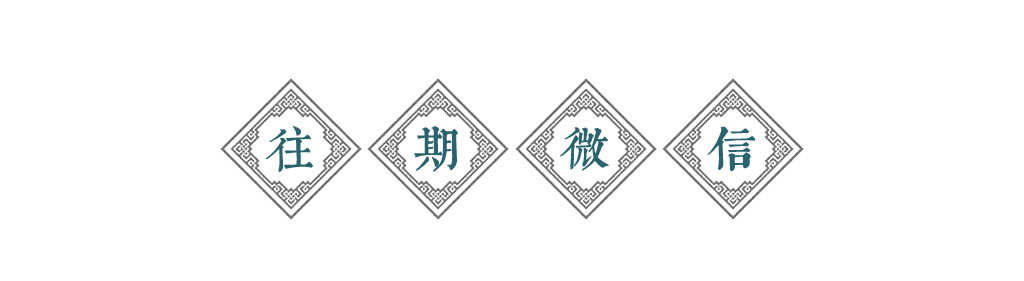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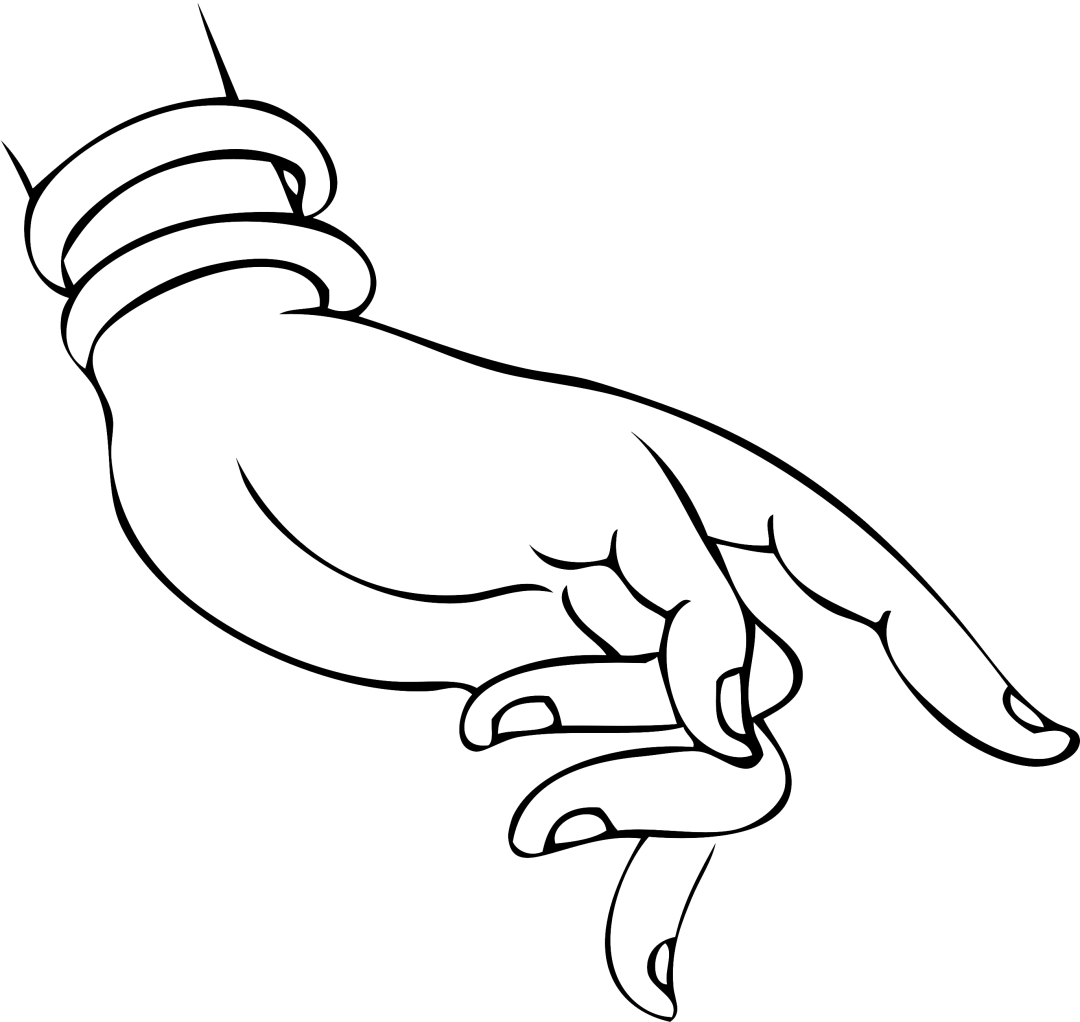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