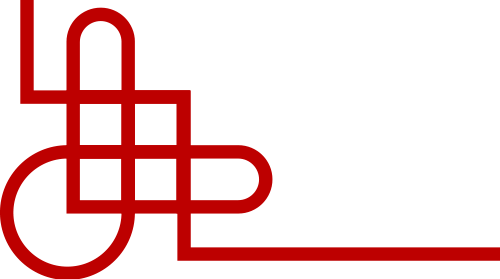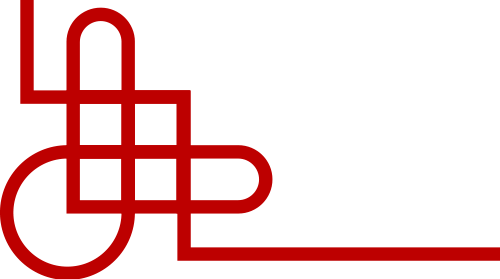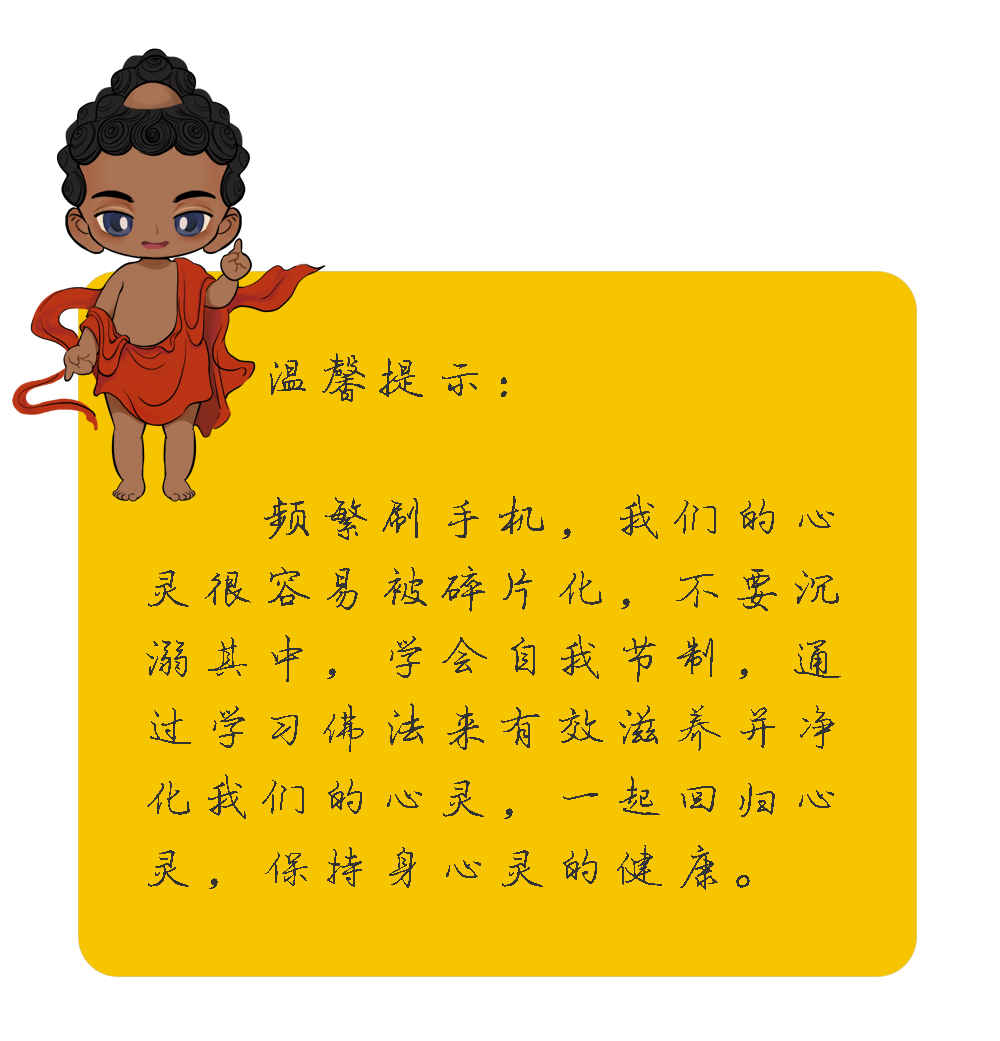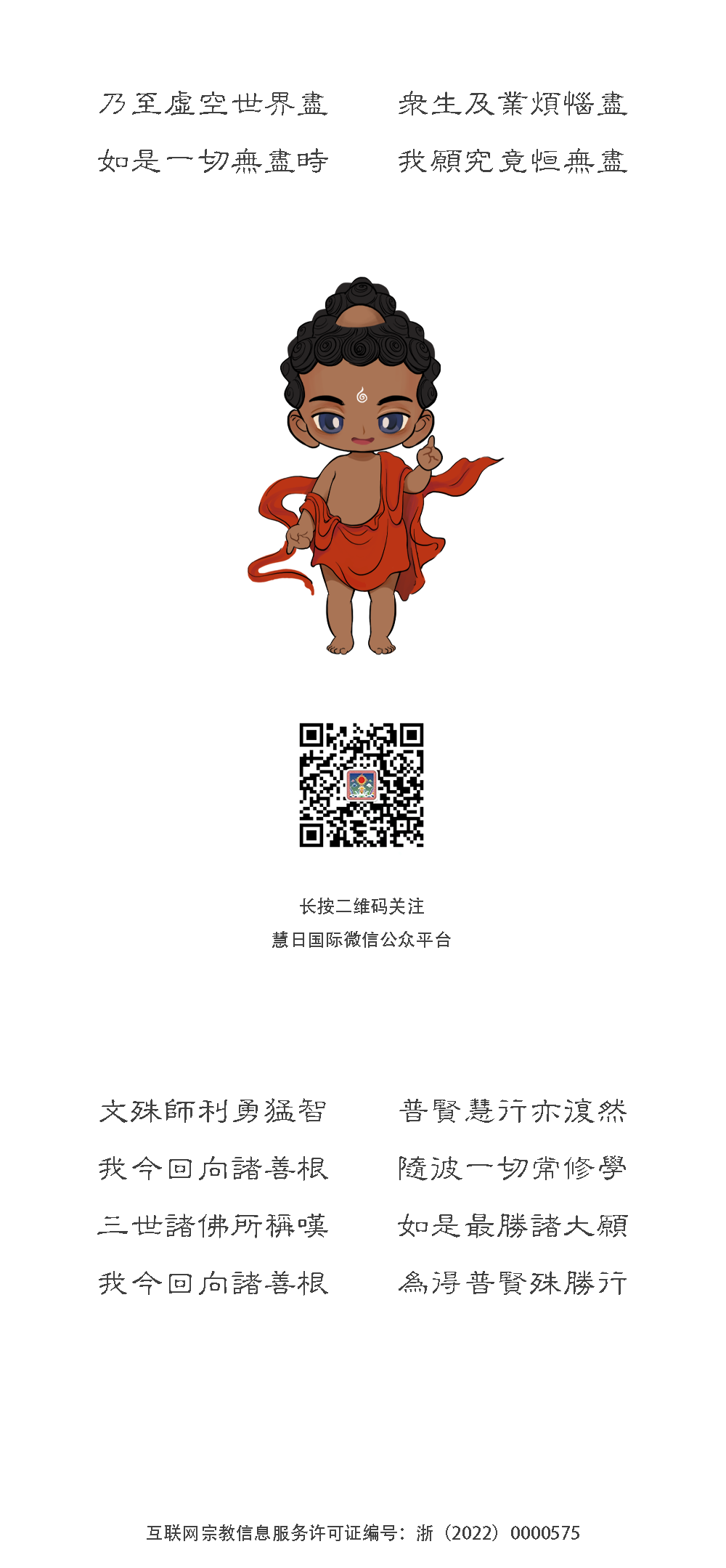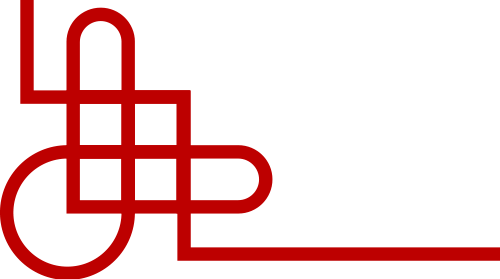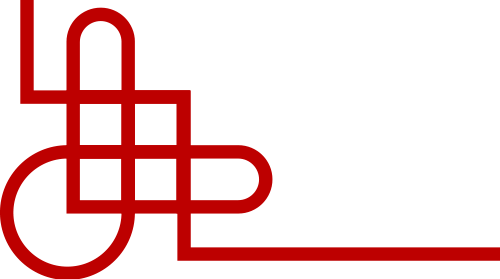新年学习《心经》消灾免难增福慧|如何获得高质量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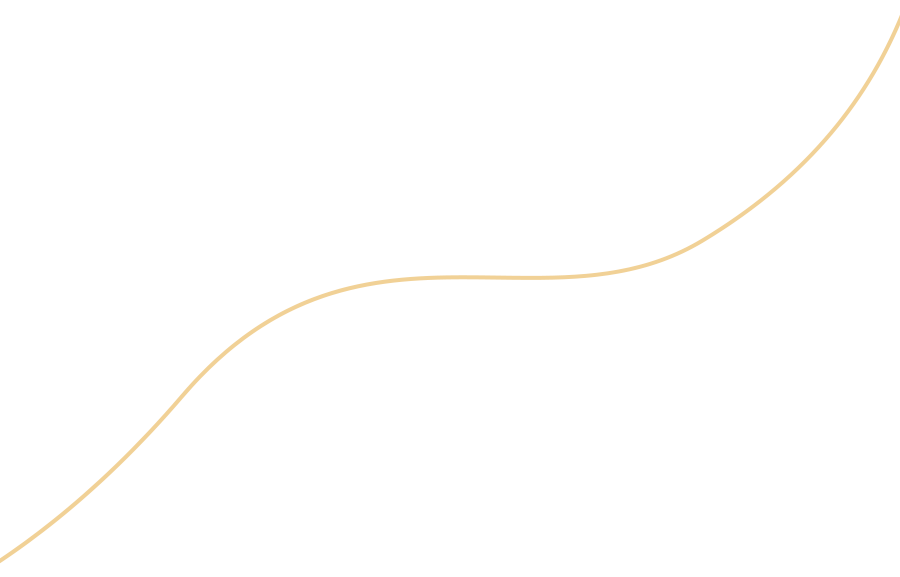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受想行识” ——五蕴,讲了一个“色法”,其余的“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受不异空,空不异受;
受即是空,空即是受。
想不异空,空不异想;
想即是空,空即是想。
行不异空,空不异行;
行即是空,空即是行。
识不异空,空不异识;
识即是空,空即是识。
当你看到“色法”的时候,是这样;当你产生“想”的时候,“想”其实也是“空”。讲木头当体即空,还不好理解,讲“想”是“空”,就好理解了。就像念佛,你心里想着佛,想着、想着就“想”到孙子了,“想”本身就不坚固,会跑来跑去,“想”、“空”之间,“空”也不是“顽空”,你为什么能够“想”?是因为你的如来藏性、佛性,恰恰展现了你佛性的面目!

“受”也是这样。“受”就是“触觉”、“感受”,“鼻子”领受“香味”,“眼睛”领受“色法”,乃至你的心“意”领受“法尘”;“眼耳鼻舌身意”其实都有一个“受”。“受”,从“触受”的角度来说,用丝绸或麻布来摩擦你的皮肤,你会感觉到丝绸的光滑柔软、麻布的粗糙生硬,“受”是要依仗因缘而生,因缘是真的,还是假的?因缘也是无常的,所以触的这个“受”是不真实的。
“行”也是这样。我们坐在讲堂里24小时,太阳升起落下就是一天。如果坐飞机,跟着太阳同一方向飞,看到太阳落山再看到太阳升起,这时还是24小时吗?就不是了,那不坐飞机,坐飞梭——航天飞机,看到太阳升了又落、落了又升,24小时能看到16次,时间就不一样了,所以“时间”即“行阴”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行阴”虽是虚妄也不是“空”,也是“妙有”。“行不异空”,当“行”的时候,就是你佛性的彰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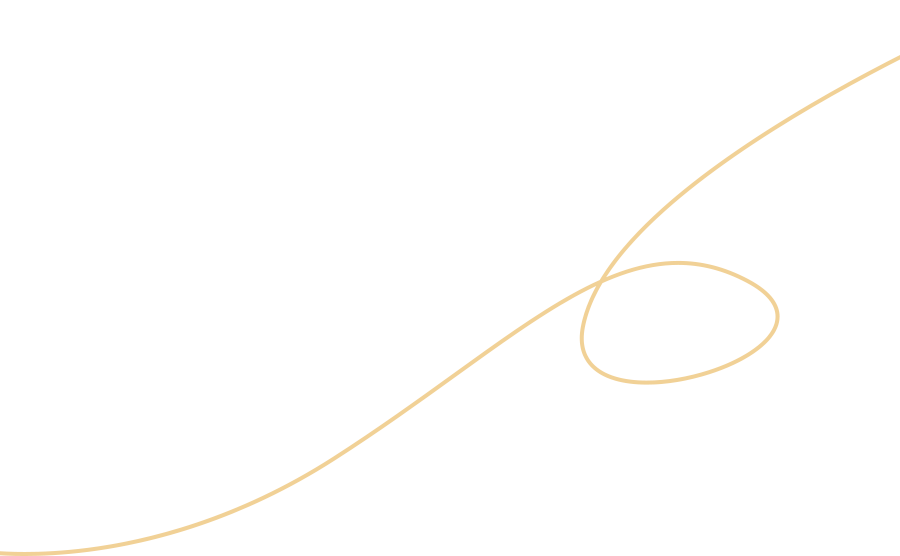

为什么叫无量光无量寿?
从哪里体现出来?
这种智慧就体现在当你“照见五蕴皆空”时,“色”是我们的如来性即佛光,“受”也是我们的佛光,“行”也是佛光,“识”也是佛光,“色受想行识”皆是我们的佛光时,那无处不是佛光,就是“无量光”。
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是:“哦,痛苦,我不要;快乐的,我要!”一辈子几十年下来,这样的生命质量就打了折扣。而修行人是面对痛苦也百分百接受,这是我的佛性,是真实的,不“住”色生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因为只要一“生”一“着”就“落”到“无明”里了,“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果在一切的显现里,皆能看到自己的佛性,你就见到佛了。
Our current state of life is like: "Oh, suffering—I reject it; happiness—I want it!" After decades of living this way, the quality of life becomes diminished. In contrast, a practitioner fully accepts suffering as well, recognizing it as the very manifestation of Buddha-nature—something real. They neither let the mind dwell on form, nor do they let it arise dependent on "form, sound, smell, taste, touch, or dharma." For as soon as the mind “arises” and “clings,” it falls into ignorance. “If one sees all phenomena as non-phenomena, one sees the Tathagata.” If, within all appearances, you can see your own Buddha-nature, you have seen the Buddha.


当我们见“色法”时就以为这是“色法”,跟自己不相干,你就落入了“生灭”。若看到“色法”:诶,这是我佛光的显现,“色受想行识”皆是我们的佛性,“五蕴”、“空”皆是我们的佛性,“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今天我们讲的《心经》,都是关于“修”和“怎么修”,不仅仅只是文字上讲讲,要这样去理解、去“观修”,是很重要的!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