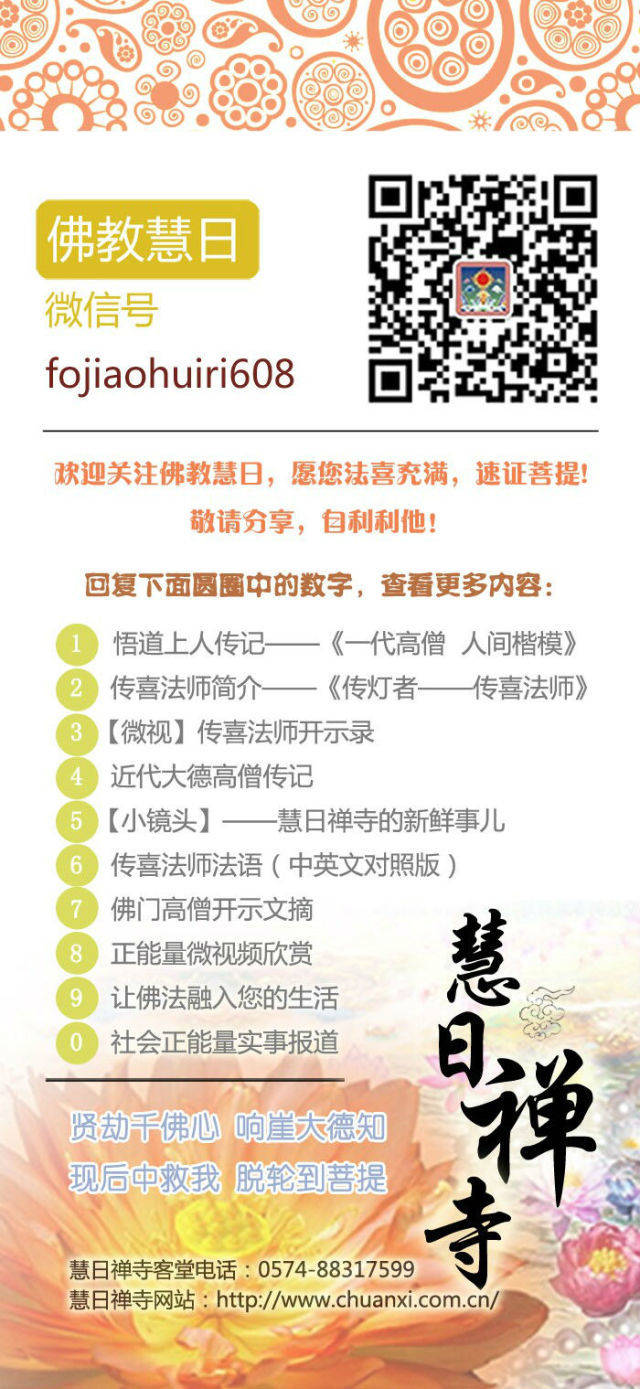傅国涌:一个人的生命能否展开,起点在基础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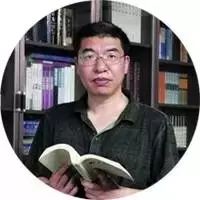
傅国涌
(原标题: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基础教育)
我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但是政治的根基在教育,所以我从政治追溯到经济,从经济追溯到教育。但我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我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关乎过去的事,历史乃是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我一直倡导,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教育,都不要走捷径,要走一条最笨的道路,脚踏实地,我喜欢用一个词“得寸进寸”。这个词蕴含着我对中国未来社会变革的一种态度,我不赞同一步登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改变了。我非常关心中国的教育往何处去,因为教育往何处去就是中国往何处去,教育到达哪里,中国的文明就到达哪里。
教育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一个人的生命能否展开,起点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如果没有学校教育给一个人提供最初的翅膀,他的生命是无法展开的。
20世纪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不少人只读过小学、中学,没有读过大学。比如范用,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总经理,是小学毕业。著名作曲家周大风,十几岁就开始谱曲,他也只读过小学。金克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小学生。
中学生里面,后来成大气候的有钱穆、叶圣陶、梁漱溟等人。他们受到的中小学教育,足够给他这样的翅膀。所以我常常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它的高等教育,而是基础教育。十几年前,我只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后来慢慢开始关注中学,2006年春天出版了一本《过去的中学》,后来就关注到小学,出版了《过去的小学》。
民国的教育家

张謇
晚清有个状元张謇,南通人,他是一个实业家,也是教育家,他有句名言叫“父教育”、“母实业”。在他看来,教育比实业更重要。他本来想办教育,但是没钱,就先办企业,挣了钱再办学校。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于1902年创立的,比官办的师范学堂要早很多。他到日本考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把门窗比例、桌椅板凳的高矮都记下来,连厕所、厨房的门都量,回来以后照着做。他发现,很多最简单的东西中国人都做不了,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他一开始就模仿日本。中国最早的教科书也是请日本人帮助编的,就是1902年到1904年完成的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
大多数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校长,今天的人已经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了,除个别像陶行知、经亨颐、张伯苓大家还知道外,林励儒是北师大附中校长,后来做北师大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这些人有的当时非常有名,但今天的我们已不知道他的名字,比如刘百川我是今年才知道,因为刚刚出版了他的《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非常精彩。王人驹的后人自编了《王人驹文集》,寄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原来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温州籍的教育家,他不光有理念,而且有实践。
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名校的和非名校的,一同构成了一个灿烂的教育家群体。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那些有名的大教育家,那个时代的教育还不一定就有多好,只有出现大量不太有名的、普通的,具有教育家气质、能力和情怀的人,这个民族的教育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
民国的校歌
民国时代的老师,普遍认为学生身上有巨大的潜能,他们愿意在一个自由、舒展、开放的状态下跟学生交流,这种交流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交流。所以,我把民国的教育称为有温度的教育。温度就是人与人之间有生命的交流,有那种爱的关怀,有怜悯。学习是一种生命状态,不是技术性的,你把它变成技术活儿,大家都会很苦。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校歌,就知道那时候的中小学是什么样的。
北师大附中的校歌是这样的:
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
你是个海啊,含真理无穷。你是个神啊,愿人生大同。
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多美好,北师大附中是中国顶级的中学,有110年历史,很多名流都从这里毕业。20年代的校歌让我们看到它的从容和自信,校歌的背后是学校,是老师、校长、学生,校歌的背后就是人。
再看天津南开中学的校歌: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锓锓,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上海位育中小学的校歌:
黄浦江,水泱泱,大小朋友聚一堂。用我手,用我脑,大家工作一齐忙。
莫怕工作忙,身心俱康强。国旗兮飞扬,庭树兮芬芳,琴韵兮悠扬。
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
人生目的不可忘,将来国事谁担当?创造,创造,生长,生长,位育意义深且长。
位育有中学也有小学,至少出过8个大学校长,有同济大学的,有北京大学的,有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校长,还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
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有点累,那个时候的初中生就能接受这样的半文言。这是他们的校长、一位数学老师写的,音乐老师谱的曲,全校传唱。
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真是到了骨髓里。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他们进攻上海,首先想炸毁的不是军事基地,而是商务印书馆,因为商务印书馆是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摧毁,这个民族就真正被摧毁了。
我的三位好老师
我从小学、中学、大学,读的都是最普通、最烂的学校,但我曾遇到过好老师。
我14岁时遇到一位老师,告诉我怎么写文章,他只教了我三句话,却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其实只教了我叙事的技术。我当时写了一篇作文,被我的语文老师看上了,她拿给她的先生看。她先生是我们县里的文章高手,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
我被叫到老师的宿舍,他跟我大约说了5分钟。他说你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他告诉我叙事的文章要怎么写,“你是写捉螃蟹,你要写——先抓大的,再抓中等的,然后再抓小的。”
当时我不大懂,只是按照他说的去修改了,后来发表了。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要这样写文章,现在我明白了,这就叫层次,这就叫具体、细节,这就叫鲜活。他教会我这个技术,我现在可以得心应手的运用,与我的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所以我可以把历史细节用好的叙事表达出来。
然后,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二位老师,他教了我好几句话。第一句,在学术上不要搞空对空导弹,要搞地对空导弹,就是要脚踏实地;第二句,写文章要以小见大,从小切口切入,写大问题;第三句话是告诫我,你要在学术上训练自己10年。他说你不要急于写东西,我对你有信心,你10年后再开始写,肯定行。其实我是过了12年才开始写东西。20多年后我更加明白了,老师说的完全正确。没有他说的这个10年论,我肯定不行。
我生命中的第三位老师是28岁那年才遇到的。我觉得时间都是对的,14岁遇到一位,18岁遇到一位,28岁遇到一位,如果没有前面两位,第三位遇到也没用。这一位,如果不是他找我,我还不敢去找他。许良英先生是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在科学史领域很有影响。他找到我,给我很多批评,当然也给我一些鼓励。但是他的鼓励带着温度,我知道他很喜欢我,他的批评有一些我听不进去,但我很喜欢他的批评。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交往,一直到现在,他已经92岁了。我28岁以来很多方面都受益于他,我们几乎每月都会通一封信。他不喜欢打电话,喜欢写信,这是老辈知识分子的习惯。他给我的信可能有好几百封了,我们什么都谈,谈思想、谈学问、谈人,谈中国的事,谈世界上的事……我1995年认识他,4年之后,1999年我开始写东西。
我的故事没有普遍性,但从中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生命中,假如在小学就遇到一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老师有多重要。
金庸就遇到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给他的教诲影响到他几十年后办报。很多人都说,小时候的某一位老师、某一件事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专业的方向、最后的造化。汪曾祺母校的校歌里最后那句话,真的非常棒“他日毋忘化雨功”。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创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随喜转载,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