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中,那些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慈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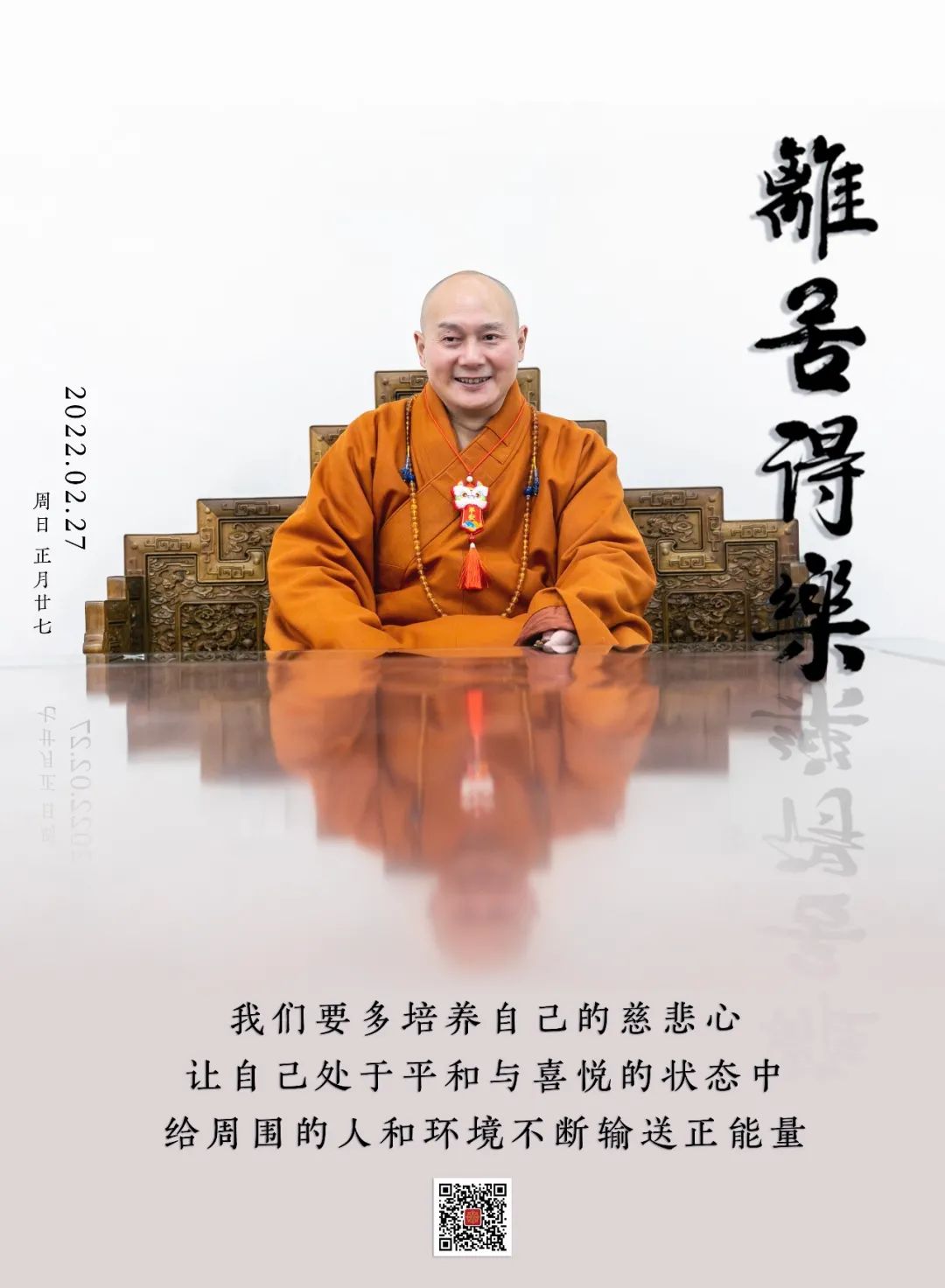
在中华文化最鼎盛的大唐盛世,却出了不识字的六祖大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超越了文字的智慧,现量地呈现了佛法的不可思议。这种智慧,寒山大师称为“无物堪比伦”。
●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
——唐 · 寒山大士
《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老子形容自己对大道的体悟,这个“常名”就是形容大道之象的特殊性了。
佛弟子虽然有时候用文字来梳理自己的思路,但是还要有一种超脱,有一种不执着文字的智慧。

我体验过,当静下来的时候,真的可以文思泉涌、一泻千里。所以就可以知道那些高产的作家伏案疾书,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创作出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个高产的音乐家在创作的时候,音符就像在他的五线谱上跳动一样,他就可以记录下来。
一个人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是自然而然的产物。对世间人来说,这是很高超的境界,但是对修行人来说,不能着在这个境界里的。《楞严经》讲“若作圣解,必落群邪”。如果你体验过了,不仅不会执着世间的成就,也不会执着出世间的成就。

什么是出世间的成就呢?就是心无所着。贪求世间的名誉会着魔,贪求出世间的所谓的开悟了、得道了……这是大魔。
比如说,一堂禅七打下来,方丈考功课的时候问:“你悟到什么了?”大家都静静的,不管是几十人、几百人乃至几千人,个个都是心平如水。
不着名相,不作圣解,这是一种大解脱,也是一种大庄严,这说明正法还住在人间。我们的心光已经超越了世出世间一切名相,这就是一件最吉祥的事。
如果有个人非要说自己悟到什么了,这就是魔,心里面像有只兔子一样,咚咚咚~地要跳出头。
虚云老和尚说:“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这都是后来对这个法的一种记述吧,这在禅堂里是不可能说的。那个时候就是“虚空粉碎也”,我、我所,一切的所谓的空、色,所有二元的对立,都顷刻间桶底脱落,大地平沉。
●
一夕夜,放晚香时,开目一看,忽见大光明如同白昼,内外洞澈,隔垣见香灯师小解,又见西单师在圊中,远及河中行船、两岸树木,种种色色,悉皆了见。是时,才鸣三板耳。翌日,询问香灯及西单,果然。予知是境,不以为异。
至腊月八七第三晚六枝香开静时,护七例冲开水,溅予手上,茶杯堕地,一声破碎,顿断疑根,庆快平生,如从梦醒。
因述偈曰:“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
摘自《虚云和尚自述年谱》

什么是三界?“我”就是三界,“我执”就是三界,习气就是轮回。我执破的时候,就是轮回的牢笼破了。
为什么古人写书的时候,最后都要写上“请名家斧正”?而且还会来一句,“个人拙见,很不成熟,贻笑大方”。什么叫大方?就是明眼人,高人。一落于文字就会有一种惭愧,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
所以我们跟师父说:“我们给您老人家出本书。”师父总说,“佛经那么多,祖师传那么多,都不愿意看”。他不会觉得一定要落个笔,要写本书,纵是要写,也是不得已。
虚云老和尚开示的时候,一上来总要讲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是上根利器的话,哪有这么多啰嗦?真的是拖拖拉拉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禅宗里也会讲,众生是因为有苦、有轮回,不得以才有法的。众生因为有病才需要药,一个好的医生的愿望就是:天下若无病,宁愿药生尘。有些法师也说自己本来很内向,不喜欢说话的,也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但有时候就是一种因缘,不得不说。
不仅禅宗的祖师有这个风格,各派的法师往往都是这样的。佛陀在涅槃前也是这样讲的,祂说不要说我说过一个字,说我说过一个字,那你是诽谤我。

所以我们每天祈求着文殊菩萨加持我们,能够净除习气垢染,培植殊胜的福报,于三宝生起不退转的信心,于佛法得定解,于佛法得受用;能洞穿轮回的虚假,能触摸到解脱如金刚地基般的坚固和真实,也能看到众生沉沦于苦海而生起不忍,这样我们此生的人身就是最庄严殊胜的了。

我于十方佛,合掌诚祈请:
为众除苦暗,请燃正法炬!

回 向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长按二维码
关注我们
你要做的
无非是
开始和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