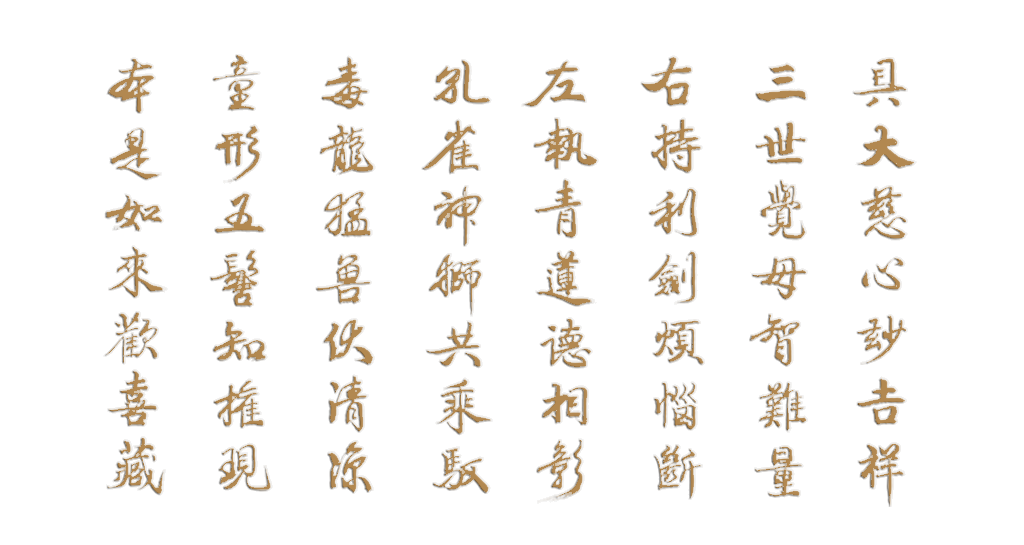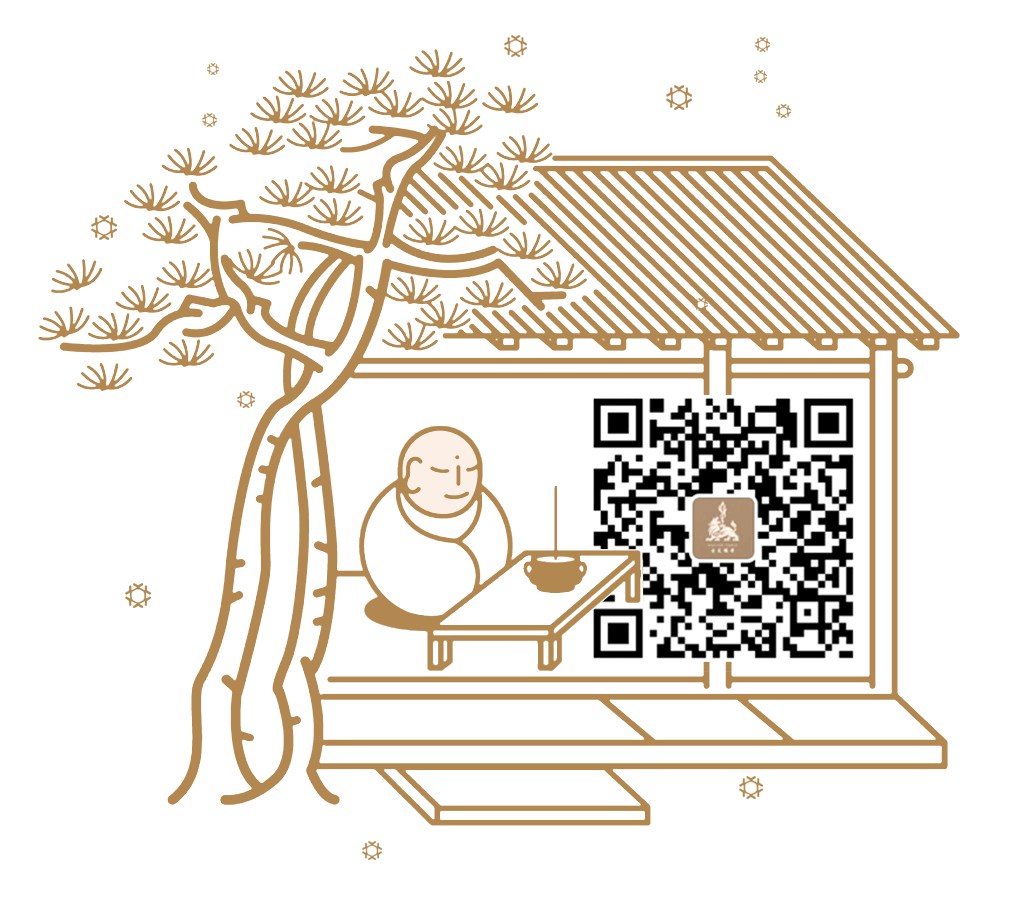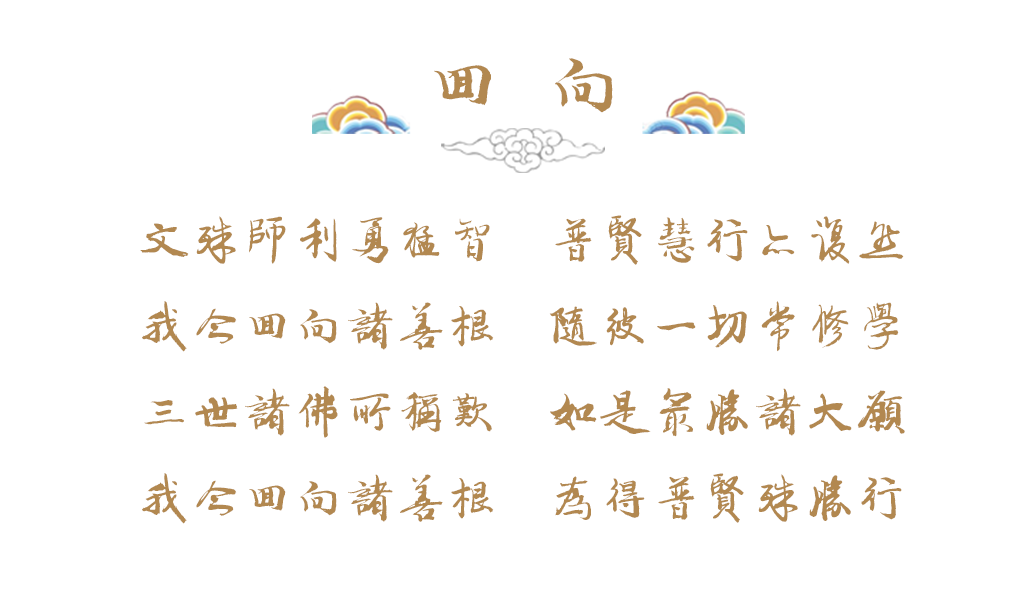石佛之缘:中国早期石雕造像欣赏之三

中国早期石雕造像欣赏

佛教造像与一般雕塑创作有别,并非以对美的追求为终极目标,而是透过具体的形象来传达佛教教理与思想。《大智度论》卷第二载:“佛陀,秦言智者。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菩提树下了了觉知,故名佛陀”,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意,因此佛陀容貌庄严殊胜,经典中称之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诸佛法相的基本仪轨。

隋彩绘贴金观音菩萨石像
隋彩绘贴金观音菩萨石立像,即是此次出土窖藏佛像中最为精美的一件,体现了当时泾川佛教文化的兴盛和造像工艺的发达。

隋代
观世音菩萨立像
圆雕菩萨,头戴盛饰大、小团花间云纹及平行线条的华丽宝冠,冠带在双耳上方打结后向两侧下飘至双肩。面相丰满秀美,方颐,双目微微闭合,鼻梁直挺,鼻翼较宽,鼻尖残缺,双唇微闭,显示出菩萨庄重严肃的神情。颈饰带铃的宽带形项圈,双腕戴双条形镯,胸佩由三排小联珠纹、小团花等组成的华丽而精致的璎珞,璎珞自双肩下垂至膝部用一团花串联成环形。观世音菩萨裸露上身,斜披络腋,下着贴体长裙,腰系裙带,裙带在腹前挽一花结,肩披红、绿、兰三色帔帛,帔帛由两臂下垂交叉于下腹前,形成“X”形、交叉处有一环状饰物。

观音菩萨跣足立于圆台上,台高4厘米,直径20厘米,台底下有高7厘米的圆柱形榫是为固定造像所用。造像比例匀称,体态健美,躯体微曲,左手曲举执拂尘,右臂从肘部向前抬伸,手持净瓶。从造像的表现技法看,线条较为稀疏,下部有稀疏的衣褶,雕刻技法正处在由直平刀法向圆刀刀法的过渡阶段。

张波造石弥勒佛像
隋开皇五年(585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背屏一佛二菩萨三身像。佛像肉髻低平,方圆脸,嘴宽,唇薄。身材颀长,腹部略向外挺。着双领下垂袈裟,阶梯状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赤足立于宝装覆莲座上。佛两侧为菩萨,头戴三叶冠,宝缯从两侧叶中穿出垂在肩前。戴桃尖项圈,披帛在上腹处系结后上绕到手臂外侧垂下。下着裙,系带下垂,赤足立于由莲叶撑起的圆台上。二菩萨内侧手胸前持莲蕾,外侧手腿侧持桃形物。下为长方形基座,正面刻出平台。中央为半身地神双手托举博山炉,炉两边有莲叶,外侧为正面侧身蹲坐的狮子。发愿文刻在右、后两面,为“开皇五年七月廿七日,为亡息张文学敬造弥勒像一区,张波为息。”

隋代佛坐像
上海震旦博物馆藏
佛教造像与一般雕塑创作有别,并非以对美的追求为终极目标,而是透过具体的形象来传达佛教教理与思想。《大智度论》卷第二载:“佛陀,秦言智者。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菩提树下了了觉知,故名佛陀”,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意,因此佛陀容貌庄严殊胜,经典中称之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诸佛法相的基本仪轨。

这尊石灰岩质佛坐像着偏袒右肩式袈裟,结跏趺坐,法相庄严,神思安详,兼具 “顶上肉髻相”、“眉间白毫相”、“两颊隆满相”、“身形端直相”及“足下安平相”等殊胜容貌。佛像头部残留有部分早期贴金妆彩痕迹,左肩处勾钮式结带为隋代造像常见装饰,整体造型简练典雅。

隋代造像融合北齐优雅细致与北周质朴敦厚的艺术样式,并加入新时期审美观,形成崭新而成熟的造像风格,为此后唐代造像写实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仁寿二年
曲阳修德寺出土
故宫博物院藏
二菩萨头戴三叶花蔓冠,头光相连,长圆脸,长眉细眼,高鼻梁,相貌沉静自然。一手食指支颐,一手抱足踝,半跏趺坐,一足踏莲台,姿势相同,左右对称。两侧立胁侍弟子。基座前面雕刻化生童子托博山炉、护法狮和力士像,背面刻发愿文:“仁寿二年五月廿四日佛弟子雷买为亡父母敬造白玉像一区 (躯)上为皇帝及众生得离苦”。

阿弥陀佛
隋代开皇5年(公元585年)
来自中国河北省韩翠村崇光寺
隋朝,公元585年。尽管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佛教是外来宗教,其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有时会发生冲突。佛像经常与中国的图案相结合,反映出佛教的适应性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大部分中国雕像都是佛像。隋朝(公元589-618年)的两代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据史料记载,他们曾创造和修复了许多佛像。这尊阿弥陀佛大理石像(又被称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佛陀)就是其中的一件作品。根据莲花基座上的铭文可知,这尊大佛于开皇5年(公元585年)被供奉在河北省韩翠村的崇光寺。佛像的双手已经丢失,但是右手臂可以向上抬升,手掌向外做出保证的手势(佛语中的施无畏印)。左手位置较低,做出慷慨大方的手势(佛语中的与愿印)。阿弥陀佛大理石像外形非常坚固,佛衣有非常平整的褶皱,具备隋朝佛像的典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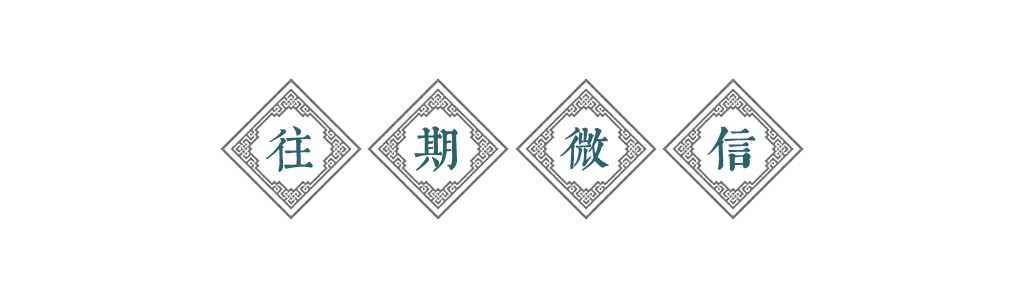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