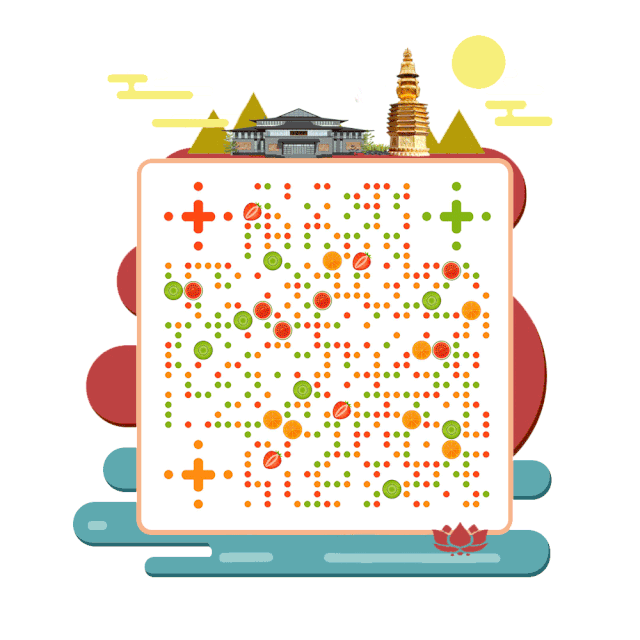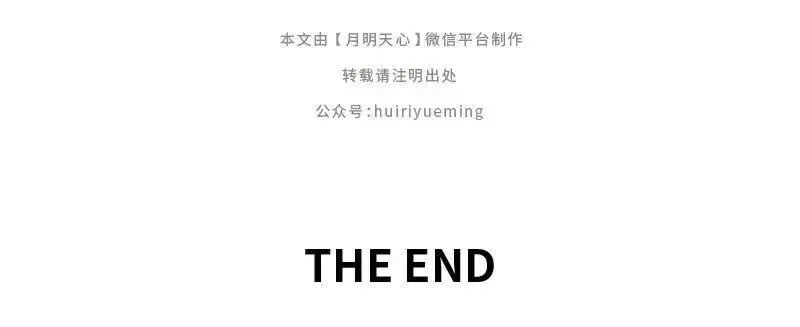这个端午节,让我们修身积德,链接起端午正大光明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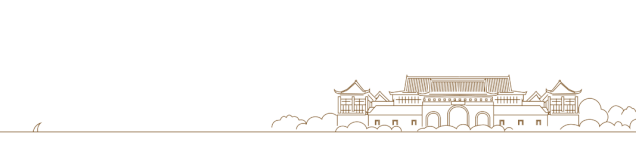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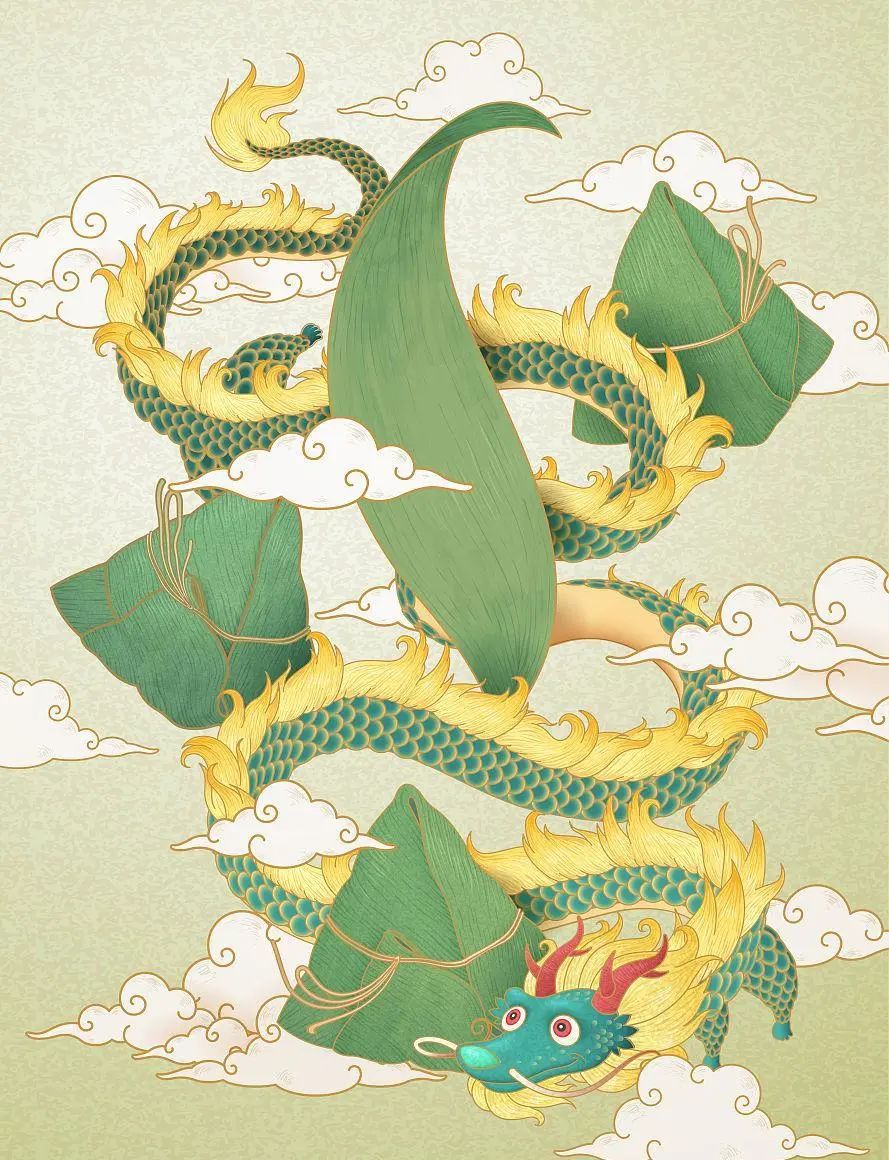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至。按十二地支的顺序推算,农历五月是“午月”,而午时又是“阳辰”,所以端午节也叫端阳节。
身正为端,德高为阳,端午应该是正气浩荡,光明煊赫的日子。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虽众说纷纭,在纭纭众说中却总有江水勾连起人们忧伤而湿润的情意。在千百年的约定俗成中,人们愿意相信端午与屈原有关,与伍子胥有关,与曹娥有关,而这三人都以忠孝之节身归江流。
宁肯高洁于水底,不愿苟且于世间,这是屈原的志怀;分明忠谏于君王,岂料抛尸于钱塘,这是伍子胥的悲愤;巨滔吞父于舜江,烈女嚎啕共赴死,这是曹娥的孝节。无论屈原、伍子胥,还是曹娥,即使魂入寒江时有怨也有愤,他们的怨愤也是光明正大的,上是为国家君主,下是为高堂父母,节义持中,因而成就万古悲风。

端午节俗知多少
千百年来,端午节俗几经变化,这些端午节俗,大多数寓意着远离邪秽,祈求安康,其中还有很多表达了对孩子的美好祝愿。
食粽子
粽子在古代文献中又被写作“角黍”,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在南北朝时期,粽子还是夏至日的时令食物,在历史流转中,今天,粽子已是端午节必备美食。
划龙舟
“龙舟”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古书《穆天子传》“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划龙船时,多有龙船歌助兴,歌声雄浑壮美,扣人心弦,即“举揖而相和之”之遗风。
悬艾草
艾草寓意百福,端午前后,人们将艾草绑成一束,插于门楣,期望艾草的香味可以驱除疾病,辟除邪秽。
端午前后多雨潮湿,病菌容易滋生,悬菖蒲、艾草等确实可以借助它们挥发的气味清洁空气,消除病毒。
佩香囊
古人在端午节时,还会佩带精心制作的香囊。玲珑剔透的衣香粉荷包和香袋,内装芳香馥郁的药物如白芷、丁香等,其香气具有驱蚊辟秽的功效。
亦有心灵手巧的母亲用五色花布做成小辣椒、小黄瓜、胖娃娃、小纱灯和小粽子等各式各样的小玩物,挂在孩子的身上,据说也是为了驱除瘟疫。
缠五色线
五色线又叫长命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代表五行五方,有吉祥的寓意。在端午这一天,给孩子手腕、脚腕上拴长命缕,在大雨或洗澡时,解下抛到河里,希望河水把瘟疫、疾病冲走,以此来表达保安康的美好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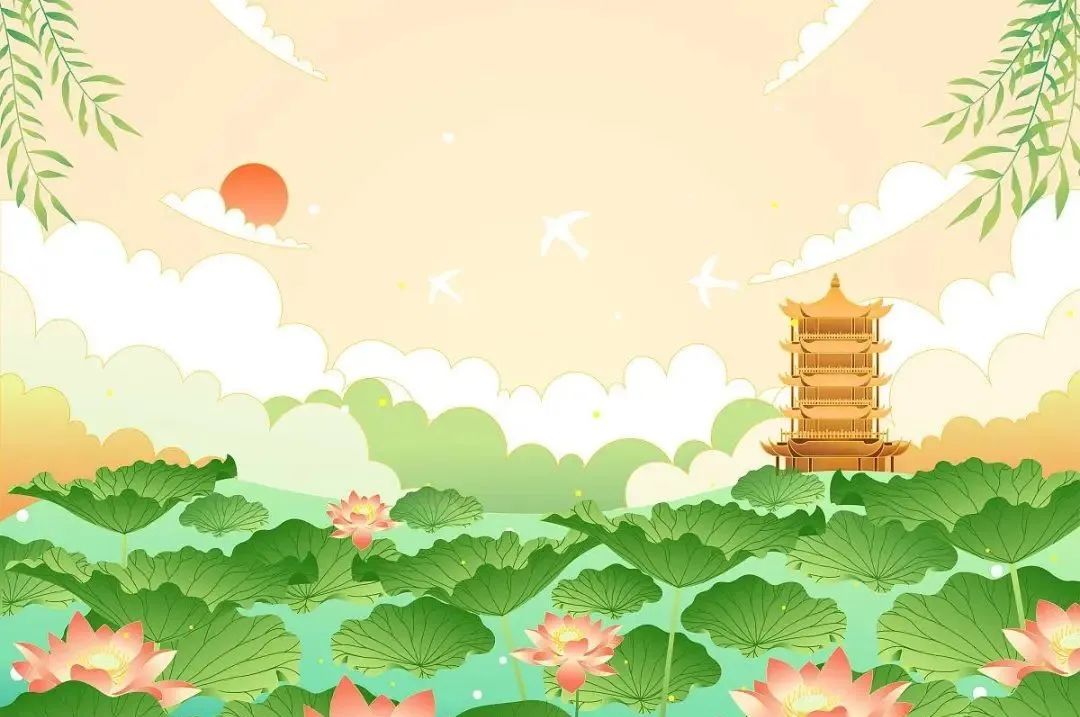
三参法师开示
在历史长河里,每年端午,总有一个话题被重提、被深思。我们在这一天纪念屈原、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纪念祖先中有浩然正气的人。他们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展现了生命的志向、孝道和气节。
在这些关于端午节来历的种种说法中,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就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中华民族是重大义的民族。对屈原的爱戴与怀念,也全然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千百年来,一个个投入水中的粽子,寄托着民众对高尚情操的祭奠和怀念,承载着对崇高精神的深深呼唤、对博大胸怀和高尚生命境界的无限向往。
而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尽忠报国、杀身取义、舍身成仁的精神,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一代一代地传承着,维护着江山社稷,造福着人民,成为华夏文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端午,“端”是端正,“午”是正午、光明。这个节日,就是提醒我们,端身正念,修光明心,让身心得以归正。哪怕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端午节吃着粽子,还是要提倡内心的苏醒。因为每个人皆有佛性,每个人的内心都本具光明的浩然之气。
对于屈原来说,他生命唯一的欠缺,就是没有学到佛法。当身心受到攻击,理想受到摧折时,如果能依靠佛法,或许就能突破生命的困境,获得更完美的人生。
屈原投江前,曾在江边遇到一位渔父,这样对他说:“圣贤的人,都不凝滞于物,而能顺随世俗的变化。举世混浊,为什么不随着潮流而去?众人皆醉,为什么不一同吃那酒糟喝那薄酒?为什么要坚持高尚的节操志向,却使自己被放逐呢?”仔细想想,这未尝不是天地有情的一场点化。
就像佛陀,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个五浊恶世,但他教导我们,先自清、自觉,从这个“浊”里出离出来,自我清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但这个自我完善的目的,并不是要离群索居,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是发菩提心,“和其光、同其尘”。与佛“和其光”,与颠倒迷惑的众生“同其尘”,做众生不请之友,与他同事、同行、同语,和他相同地生活,潜移默化地摄化这个世间。这是佛教的智慧。
我们要有屈原洁身自好的精神,同时也要有佛法的智慧和慈悲的状态。对内,有知大体、顾大局、明辨是非的智慧,保持守身如玉的高尚品格,有高度的自律;对外,要有慈悲宽广的胸怀,满怀包容之心,把自己培养成正义的力量,默默地守护世界,守护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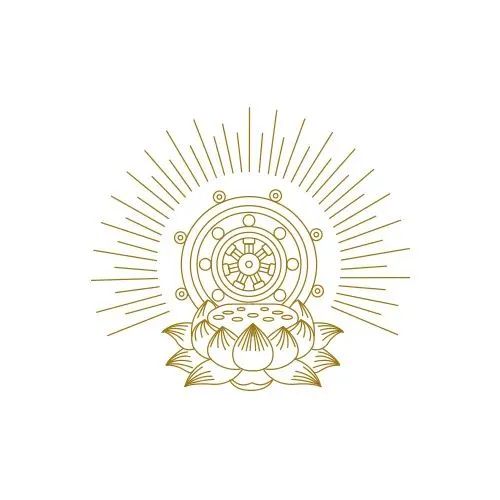
在这个端午节,我们修身积德,在天地间“充电”,链接起端午正大光明的力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能皈依一种精神的高度,都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甚至能践行在一种正确的追求上,这是人类最需要的力量。修行也需要这个力量。行端影直、光明磊落,让身口意放射出真理的光芒,乃至有一天,能够做苦海的舟航、险峡的桥梁、黑暗的明灯、迷乱世界的依怙,这样的生命才算得上不错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善得此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