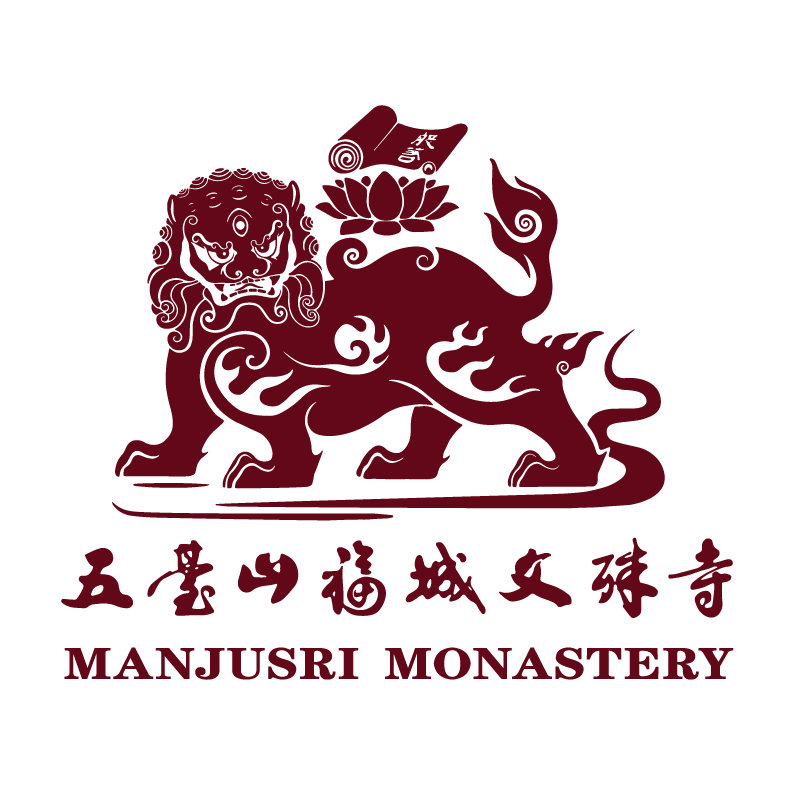玄奘大师传83|明濬回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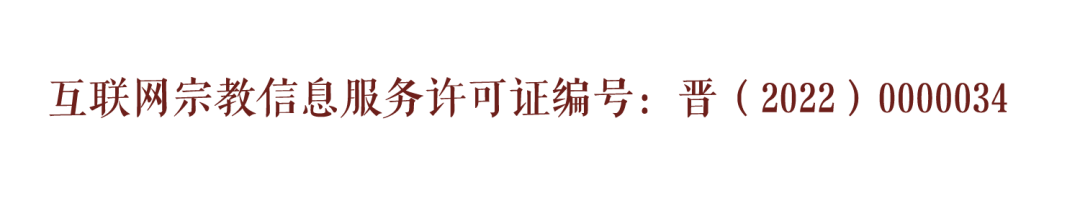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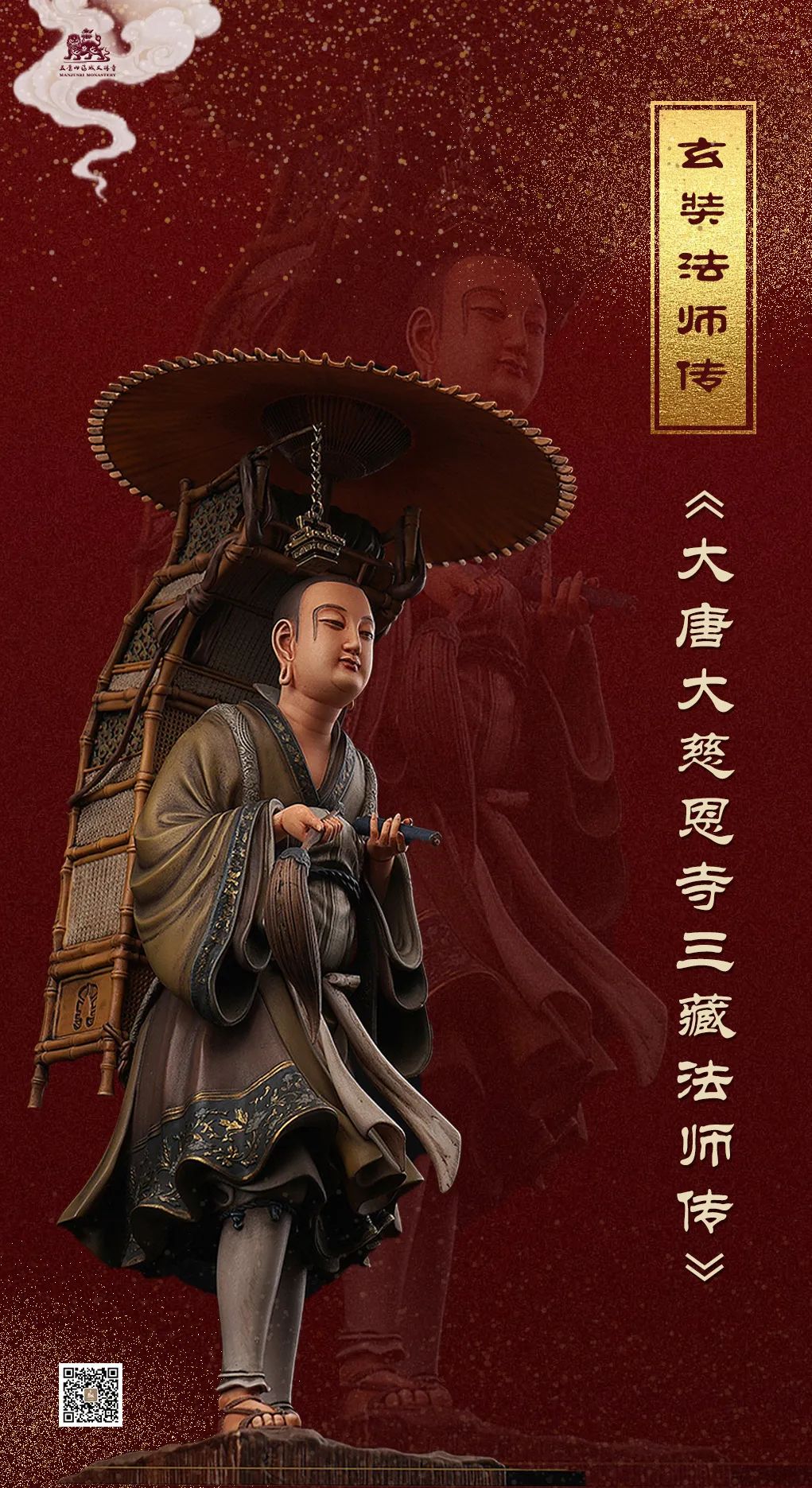

内容提要:
第八卷记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玄奘大师与吕才对定因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高宗令大臣于志宁等赞助译事,并制大慈恩寺碑文。

第八卷
83 明濬回信
译文:
四月,译经僧明濬答复博士柳宣,用自己撰写的《还述颂》来指出他的错误。偈颂说:
于赫大圣,种觉圆明;
无幽不察,如饷酬声。
弗资延庆,孰悟归诚;
良导可仰,实引迷生。
百川邪浪,一味吞并;
物有取舍,正匪亏盈。
八邪驰锐,四句争名;
饰非滥是,抑重为轻。
照日冰散,投珠水清;
显允上德,体道居贞。
纵加誉毁,未动遗荣;
昂昂令哲,郁郁含情。
俟诸达观,定此权衡;
聊申悱悱,用简英英。
《还述》文中说:
“近日收到柳宣的来信,先看了下《归敬》的文辞。阅览雄健的文章,真是光彩四射,何其宏伟壮丽啊!详考其高雅的意趣,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可悲啊,贪爱的欲望如同大海般汹涌滔天,邪恶的妄念如同高山般遮蔽天日。执着于人我差别的人,在轮回中不断堕落何时能止?依仗傲慢与执着的人,在苦海中沉沦永无尽头。因此六十二种邪见如同荆棘丛生般盘踞人心,九十五种外道如同拄着拐杖迷失方向般忘失归途。
如来以自己的大悲本愿,无缘大慈,俯身回应众生。内在圆满具足四种智慧,外在显现六种神通,运用十力以降服天魔,施展七种无碍辩才来摧伏外道。穷竭这爱欲大海,用三空门济度含识众生;摧毁那邪见的险峰,引导众生依八正道回归清净本性。指示因果,返本还源,真是伟大啊!大悲大智的妙用,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啊。
往昔佛陀于菩提树下证道,将真理之音传遍三千大千世界;涅槃后弟子们继承遗志,让佛法精神震烁寰宇。自佛教在印度式微,其智慧光芒却东照中土——周朝有“昭王见瑞”的灵应,汉代现“明帝梦金人”的征兆。摄摩腾、竺法兰率先点燃智慧火炬,佛图澄、鸠摩罗什续传法灯于后世。他们翻译经典弘扬佛法,以神通救济乱世,用妙论降伏邪说,借禅定安定人心。弘扬佛法的人相续不断,维护圣教的人比肩相随,海内外无不敬慕其德风,天人也都辅助教化,因此事业繁荣兴旺,长盛不衰。关于这一点,大家都能略知梗概。
当今玄奘三藏法师天赋灵秀,融会贯通佛法真谛,如瓶中倾泻般传授五乘教义。悲叹佛陀圣教日渐遥远,忧虑后世教法多有缺漏,于是发愿求取完整经义,以身许法。独自思虑筹划,形单影只踏上征程,振衣持杖,远赴天竺求取真经。西出玉门关跋涉万里,终至恒河畔稍事休整。在印度寺院考辨经义,深入探究佛法精微,后携经返回中土,弘扬正法破除谬误。使散佚的佛典重归完备,令大乘圆教发扬光大。
法师所弘扬的殊胜教义,绝妙至极,超越一切相对概念;揭示的真如空性,突破所有形相束缚。若执着“有”的层面,反而丧失真实;若偏堕“无”的极端,实则损害真谛。超越“空”“有”二边,忘却中道名相,这般深奥义理非寻常思维可及,重重空观终达究竟圆满。实在是精妙绝伦,至为宏大!
这般精纯的义理核心,岂是仓促间能详尽道明?玄奘法师凝聚心神穷究真知,考辨源流梳理脉络,校勘深奥典籍,开启幽微法门。如秘藏的法音随叩击显应,似浩瀚的义海纳百川归流。于是各国博学大德,异域高深僧众,皆心悦诚服前来问法,带着积年疑惑请求开示。如同饮河之水难测其渊深,听闻妙音怎知其境界?至于因明逻辑这类基础学问,现量比量不过浅显工具,不过是初学者的基本常识、立论的前提条件而已。若要触及佛法核心密钥,证悟究竟圆满实相,还需深入浩如烟海的奥义经藏,这些精深境界就非此处所能尽述了。
吕奉御气度超凡脱俗,早年便显露出多方才华。学识渊博贯通古今,少年时即彰显博物之才:既能广泛涉猎古籍典章,又能深入钻研艰深文献,触类旁通间穷尽各类术数。在辩论场上掀起思维风暴,于翰林院内绽放智慧光芒,犹如天马行空引领思潮,在京城学界首屈一指。五行学说经其修订更臻完善,六爻占卜待其阐释方显精妙,通读扬雄《太玄经》即能答疑解惑,研究象棋博弈即刻破解玄机。其才学堪比晋代张华再世,汉代东方朔重生,当今之世无人能及。
吕奉御虽在诸多学问中游刃有余,仍有余力崇敬大乘佛法,早年便怀虔诚信念。偶然因同门戏言激发,突然专注研究因明逻辑,却未寻师问道,仅凭己见穿凿附会。比对各家注疏时,妄加指摘求全责备。在朝堂引发争议,于仓促间妄下论断。考察其志向固然值得称道,但细究其学识实存谬误。这部论著仅一卷五章,研究三篇注疏竟耗时七年,所列四十处批驳竟无一处成立。
自己本无正见却妄断是非,注疏原无谬误却强加指摘。所谓“批判错误”实非真错,所谓“确立真理”亦非真谛——认为是错的却不是真的错了,认为是对的却不是真的对了。认为对的却不是真的对了,那么对的也恒常是错的了;认为错的却不是真的错了,那么错的也恒常是对的了。否定错误的观点恒常是正确的,不因为你错误的否定而否定。吕奉御由于贬斥失当,导致各种错误。
首先,从生因和了因关系来看,吕奉御认为两者是一回事而不知道二者的含义不同;不能区分能了和所了,使用同一个名称来表述而不知道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法。还有,不能区分宗依和宗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宗体,误以为宗依就是宗体;不能区分喻体和喻依,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喻体,误以为喻依就是喻体。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真是白白生起各种疑误啊;从一开始的立论前提就错了,于是便生起各种错误的论点。吕奉御只因喜欢而研究因明二论,但是他师心自用,没有弄明白上下文句的语意,混淆字音的平声去声。又把“数论”误作“声论”,将“生城”误作“灭城”。岂止误解了因明格式的离合关系,就连语言文字的前后顺序都搞错了。又用汉语的民间俚语和讹传的音韵,来比拟梵语的啭音,虽然广引七种,而只相当梵语的一啭。但却不是梵语种的七啭音,仅是第八种呼声而已。错讹杂乱如此之多,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又案《胜论》主张世界是由极微的原子组成的,原子数量无穷尽,体积又极其微小;后来两个原子之间逐渐结合,形成二重原子。恒常存在的原子数量则减半,体积则比原来增大一倍。如此原子之间不断结合,多重原子的集聚便形成了各种形态的大千世界;穷究胜论的核心理论,只是无穷无尽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原子。
吕奉御引用《周易·系辞》中所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认为这两种理论言语虽有差异而道理相同。如今考察太极无形生成有形,元气生成万物,岂能把一生多的太极说来比附多生一的原子说呢?旁征博引来显示自己见识广博,但是由于义理相违背,这种征引又有什么用呢?
所征的著名例证,生生之义貌似相同;如果解释的如同邪见,因而被深深拖累,又如何自免呢?岂能苟且贪图时下的虚名,混淆正邪是非,如果不是对自身有仇,怎么会到这种地点呢!凡所纰漏错误,怎么能说得完!只是由于率性而为,导致如此狼狈。树根既然不正,枝叶自然倾倒,于是便产生各种疑误,又随疑设难;身体弯曲而去求起立的影子,能得到吗?
试举二三个例子,希望你能详察大意,不着调的错误很多,委婉答复如上。寻思吕奉御聪敏达鉴,怎么孟浪到这种地步啊!示显真俗之间的差别,犹如云泥难易,楚越一样显明;佛教宏大辽远,正法凝寂深邃,譬如洪炉并非掬一捧雪所能扑灭,渤海已岂是胶黏的舟所能渡越的呢?
太史令李淳风李君者,内心深沉神秘,襟怀邈远超世;专心精研九数,综览涉猎六爻。博考典籍图书,观瞻云气风水;鄙薄卫宏的气度不够宏大,轻视禆灶的预言不够精巧。神采飞扬,毫无凝滞;仰望实际,如同就在那里一样。既然属于吕奉御的余论,那我就回复他的问难。以真如实际作为大觉的玄躯,把无为法当作调御的法体。如果起信熏修或许可以证得,禀承自然恐怕不能成就。这恐怕是言语相似而意思却相违背,言辞相近而旨趣却差距很大。天师绝妙的道理,希望您再考虑。况且寇谦之天师,是崔浩特别推荐的;二人共同导致了佛教浩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虽说并不是像淄水和渑水混合那样,难以分辨,也是自降身份,将黄金混同于铜矿啊。
博士柳宣器宇恢弘廖廓,学部竭尽典籍索隐,用仁义庇护身体,待人接物谨言慎行。恭谨严肃啊!汪洋浩博啊!擢拔刚正的节操高入云霄,淡泊清润的名声安定地方。芳声飞扬文苑之中,身处儒林之中,采集九畴的宗义,详细研究二戴的学说。至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不了如指掌,俯拾即是。樽俎都推行其标准,法度必定等待其决定,遂令《相鼠》那样的诗歌在民间消失,《鱼丽》那样的咏叹盈满于朝堂。真是名实相副,尽善尽美啊。至诚敬重之间,禀自平素的成就;弘护圣教之心,实在是由于素怀此志。你参与这种喧哗议论,我也为之感到羞耻,耿耿于怀。所以笨拙地写了这封回信,希望能发扬光大佛教法义。如果不是学通内外,洞察他学,怎么能激扬清浊,济度世俗,匡扶佛教呢!
昔日鸠摩罗什门下,精通佛法的高僧有三千人;如今在大慈恩寺的译场中,像那样的高僧如同市场上的人一样多。我的才识平庸浅陋,忝居译场末位。早上还庆幸有所听闻,到了晚上却感到忧惧惭愧。就我所知,撰写注疏的三位高僧,都是学贯五乘之人,他们的才德难以窥测,他们的词峰难以仰望。类似商羊飞舞,必然天降大雨;词语的迅雷发出声响,恐怕连捂住耳朵的时间都没有了。大家认为,古人说:‘一根树枝就可以让鸟儿敛翅栖息,何必使用繁茂的邓林;小小池塘足以让鱼儿在水中潜游,何必需要苍茫的大海。“所以大家不以我愚钝懦弱,责令我完成回复的任务,推辞不能获免,大略陈述梗概。虽然言辞不足为取,而义理或许可以一看。回顾自己平庸才疏,更增惊悚惭愧,直接陈述答复,别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释明濬陈述
七日,柳宣收到明濬的回信,又挑唆吕奉御将此事上奏朝廷。高宗敕令各位公卿学士等前往大慈恩寺,请法师与吕奉御当面辩论。吕奉御词穷理屈,认错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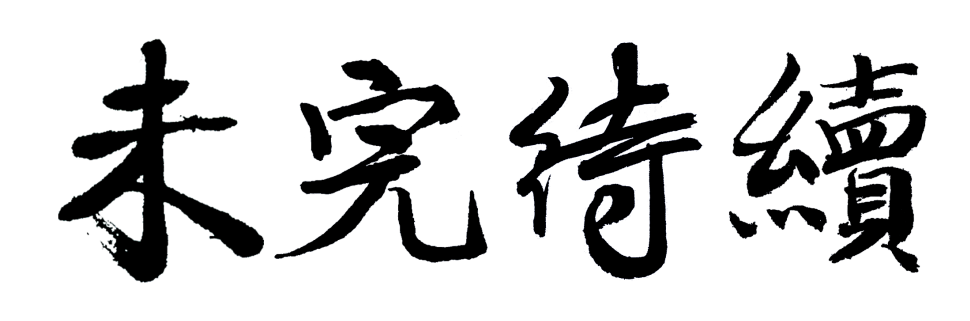
恭录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唐沙门释慧立、释彦悰撰


具大慈心妙吉祥 三世觉母智难量
右持利剑烦恼断 左执青莲德相彰
孔雀神狮供乘驭 毒龙猛兽伏清凉
童形五髻知权现 本是如来欢喜藏